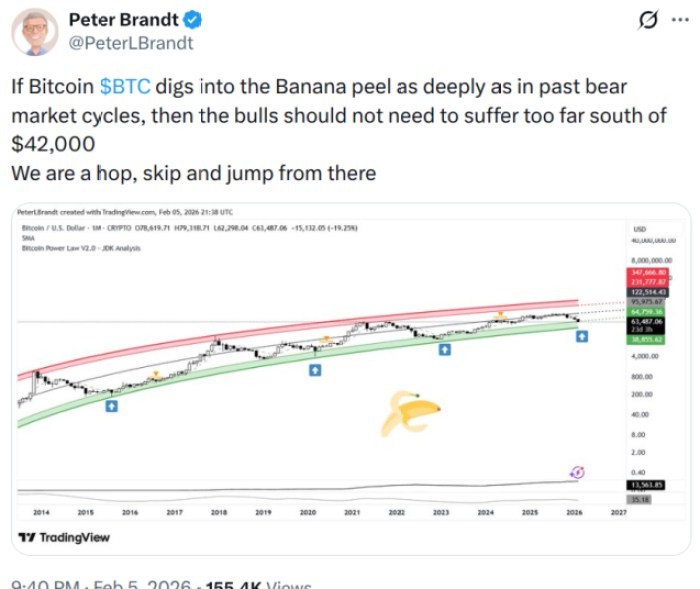作者:刘洪林
原来我根本不理解电
「五一」假期,自驾穿越河西走廊,从武威到张掖、酒泉,再到敦煌。开在戈壁公路上,公路两旁时常出现一片片风力发电机,静默伫立在戈壁之上,甚是壮观,仿佛一条科幻感十足的长城。
* 图源自网络
千年之前的长城,守的是边疆与领土,而今天,这些风机和光伏阵列所守卫的,是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,是下一代工业体系的命脉。阳光和风从未像今天这样,被如此系统地组织起来、嵌入国家战略、成为主权能力的一部分。
在 Web3 行业,大家都知道挖矿是一个再基础不过的存在,是这个生态最原始、也最坚固的基础设施之一。每一轮牛熊切换、每一次链上繁荣背后,都少不了矿机持续运转的声音。而我们每次谈起挖矿,谈得最多的就是矿机的性能和电价——挖矿能不能赚钱、电价高不高、哪里能找到低成本的电。
然而在看到这绵延千里的电力之路,我却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理解电:它从哪发出来?谁能来发电?它如何从大漠传送到千里之外,谁来使用,又该如何来定价?
这是我的认知空白,或许也会有伙伴对这些问题同样充满好奇。所以,我打算借这篇文章,做一点系统性的补课,从中国的发电机制、电网结构、电力交易、再到终端准入机制,重新理解一度电。
当然,这是红林律师第一次接触这个完全陌生的话题和行业,必然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,也请伙伴们多提宝贵意见。
中国到底有多少电?
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宏观事实:根据国家能源局在 2025 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,2024 年全年中国发电量达到 9.4181 万亿千瓦时,同比增长 4.6%,约占全球发电量的三分之一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?整个欧盟加起来的年发电量也不到中国的七成。这意味着,不仅我们有电,而且我们正处于「电力过剩」和「结构重构」的双重状态。
中国不仅发电多,发电的方式也变了。
截至 2024 年底,全国总装机容量达到 35.3 亿千瓦,同比增长 14.6%,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进一步提升。光伏新增装机约 1.4 亿千瓦,风电新增 7700 万千瓦。从比例来看,2024 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占全球 52%,风电新增装机量占全球 41%,在全球清洁能源版图上,中国几乎是一个「统治性角色」。
这种增长不再仅仅集中在传统能源强省,而是逐渐向西北部倾斜。甘肃、新疆、宁夏、青海等省份成为「新能源大省」,正在逐步从「资源输出地」向「能源生产主力」转型。为了支撑这一转型,中国在「沙戈荒」地区部署了国家级新能源基地计划:在沙漠、戈壁、荒漠区域集中布局超过 4 亿千瓦风电和光伏装机,其中首批约 1.2 亿千瓦已纳入「十四五」专项规划。
* 亚洲第一座,敦煌首航节能 100 兆瓦熔盐塔式光热发电站(图源自网络)
与此同时,传统的煤电并未完全退出,而是逐渐向调峰型、灵活型电源转化。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,2024 年全国煤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不到 2%,而光伏和风电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37% 和 21%。这意味着「以煤为基、以绿为主」的格局正在形成。
从空间结构上看,2024 年全国能源电力供需总体平衡,但地区结构性过剩依然存在,特别是西北地区部分时段出现「电多用不了」的局面,这也为后文我们讨论「比特币挖矿是否是电力冗余的出口方式」提供了现实背景。
一句话总结就是:中国现在不缺电,缺的是「能调的电」「能消纳的电」和「能赚钱的电」。
电谁能发?
在中国,发电不是一个你想干就能干的事情,它不属于一个纯市场化的行业,更像是一个有政策入口、有监管天花板的「特许经营」。
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,所有想要从事发电业务的单位,都必须取得《电力业务许可证(发电类)》,审批主体通常是国家能源局或者其派出机构,视项目体量、区域和技术类型而定,它的申请过程往往涉及多个交叉评估:
- 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的能源发展规划?
- 是否已取得土地使用、环评和水保批复?
- 是否具备电网接入条件和消纳空间?
- 是否技术合规、资金到位、安全可靠?
这意味着,在「能发电」这件事上,行政权力、能源结构和市场效率三者是同时参与博弈的。
目前,中国发电主体大致分为三类:
第一类,是五大发电集团:国家能源集团、华能集团、大唐集团、华电集团、国家电投。这些企业掌握了全国超过 60% 的集中式火电资源,也在新能源领域积极布局。例如,国家能源集团 2024 年新增风电装机超 1100 万千瓦,在行业内保持领先。
第二类,是地方国资企业:如三峡新能源、京能电力、陕西投资集团。这类企业往往与地方政府绑定,在地方电力布局中占据重要角色,同时承担一定的「政策性任务」。
第三类,是民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:典型代表如隆基绿能、阳光电源、通威股份、天合光能等。这些企业在光伏制造、储能集成、分布式发电等板块展现出强劲竞争力,也在一些省份拿到了「指标优先权」。
但即便你是头部新能源企业,也不意味着发电厂你「想建就建」。这里的卡点通常出现在三个方面:
1. 项目指标
发电项目需要纳入地方能源发展年度计划,必须获得风光项目指标。这个指标的分配,本质上是一种地方资源控制——你没有地方发改委、能源局的同意,就不可能合法启动项目。部分地区还采用「竞争性配置」方式,根据土地节约程度、设备效率、储能配置、资金来源等打分择优。
2. 电网接入
项目批下来之后,还得向国家电网或南方电网申请接入系统评估。如果当地变电站容量已满,或者没有输电通道,那你建出来的项目也没用。特别是在西北等新能源集中的区域,接入难、调度难是常态。
3. 消纳能力
就算项目批了、线路也有,如果当地负荷不够、跨区通道没打通,你的电也可能「无人可用」。这就出现了「弃风弃光」问题。国家能源局在 2024 年通报中指出,个别地市甚至因为集中上项目、远超负荷,而被暂停新增新能源项目接入。
所以,「能不能发电」,不仅仅是企业的能力问题,更是政策指标、电网物理结构与市场预期共同决定的结果。在这种背景下,一部分企业开始转向「分布式光伏」「园区自供电」「工商业储能耦合」等新模式,以规避集中式审批和消纳瓶颈。
从行业实务看,这种「政策准入 + 工程门槛 + 调度协商」三层结构,决定了中国发电行业依然属于「结构性准入市场」,它并不天然排斥民营资本,但它也很难允许纯市场驱动。
电怎么运输?
在能源领域,有一个广为流传的「电力悖论」:资源在西部,用电在东部;电发出来了,却送不过去。
这是中国能源结构的典型问题:西北有丰富的太阳和风,但人口密度低、工业负荷小;东部经济发达、耗电量大,但本地可开发的新能源资源非常有限。
那怎么办?答案是:建设特高压输电(UHV),用「电力高速公路」把西部的风光电输送到东部去。
截至 2024 年底,中国已投运的特高压线路达 38 条,其中交流线路 18 条,直流线路 20 条。这其中的直流输电项目尤为关键,因为它可以在极远距离下实现低损耗、大容量的定向输送。例如:
- 「青海—河南」±800kV 直流线:长达 1587 公里,把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光伏基地送电至中原城市群;
- 「昌吉—古泉」±1100kV 直流线:长达 3293 公里,创下全球输电距离和电压等级双纪录;
- 「陕北—武汉」±800kV 直流线:服务陕北能源基地与华中工业腹地,年输电能力超 660 亿千瓦时。
每条特高压线路都是一个「国家级项目」,由国家发改委、能源局统一立项,国家电网或南方电网负责投资与建设。这些项目投资动辄数百亿元,动工周期 2—4 年,往往还需要跨省协调、环保评估和落地安征迁配合。
那为什么要搞特高压?其实背后是一个资源再分配的问题:
1. 空间资源再分配
中国的风光资源和人口、工业严重错位。如果不能通过高效输电打通空间差异,所有「西电东送」的口号都是空谈。特高压就是用「输电能力」去置换「资源禀赋」。
2. 电价平衡机制
由于资源端和消费端的电价结构差异大,特高压输电也成为实现区域电价差调节的工具。中东部可以获得相对低价绿电,西部可以实现能源变现收益。
3. 促进新能源消纳
没有输电通道,西北地区很容易出现「电多用不了」的弃风弃光局面。2020 年前后,甘肃、青海、新疆的弃电率一度超过 20%。特高压建成后,这些数字已下降到 3% 以内,这背后正是输电能力提升带来的结构性缓解。
国家层面已明确,特高压不只是技术问题,更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。未来五年,中国还将继续布局「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」中的数十条特高压线路,包括内蒙古至京津冀、宁夏至长三角等重点工程,进一步实现「全国一张网」的统一调度目标。
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特高压虽好,也有两个长期争议点:
- 投入高、回收慢:一条±800kV 直流线投资往往超过 200 亿元,回本周期超过 10 年;
- 跨省协调难:特高压需穿越多个行政区,对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机制提出高要求。
这两个问题,决定了 UHV 仍然是「国家工程」,而不是企业自由决策下的市场基础设施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新能源迅速膨胀、地区结构错配加剧的背景下,特高压已经不是「可选项」,而是「中国版能源互联网」的必选项。
电怎么卖?
发完电、送出电,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问题:怎么卖电?谁来买?多少钱一度?
这也是决定一个发电项目是否盈利的核心环节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中,这个问题非常简单:电厂发电 → 卖给国家电网 → 国家电网统一调度 → 用户交电费,一切按国家定价。
但这个模型在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之后,已经完全跑不通了。光伏、风电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,但其出力具有波动性和间歇性,不适合纳入固定电价、刚性供需的电力计划系统。于是,从「能否卖出去」变成了新能源行业生死线。
根据 2025 年起施行的新规,全国所有新增新能源发电项目将全面取消固定电价补贴,必须参与市场化交易,包括:
- 中长期合同交易:类似「预售电」,发电企业与用电企业直接签约,锁定一定时间段、价格和电量;
- 现货市场交易:根据实时电力供需波动,电价可能每 15 分钟变动一次;
- 辅助服务市场:提供调频、调压、备用等电网稳定性服务;
- 绿色电力交易:用户自愿购买绿色电力,附带绿色电力证书(GEC);
- 碳市场交易:发电企业可因减少碳排放获得额外收益。
目前全国已设立多个电力交易中心,如北京、广州、杭州、西安等地的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,统一负责市场撮合、电量确认、电价结算等。
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现货市场的示例:
在 2024 年夏季高温时期,广东电力现货市场出现极端波动,谷段电价低至 0.12 元 /kWh,峰段最高达到 1.21 元 /kWh。在这种机制下,新能源项目如果能够灵活调度(如配备储能),可以「低价存电,高价卖电」,获取巨额价差收益。
相比之下,仍依赖中长期合同但缺乏调峰能力的项目,只能以每度 0.3-0.4 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电力,甚至在部分弃电时段被迫零价上网。
于是,越来越多新能源企业开始投资配套储能,一方面用于电网调度响应,另一方面用于价格套利。
除了电价收入,新能源企业还有几项可能的收入来源:
1. 绿色电力证书(GEC)交易。2024 年江苏、广东、北京等省市已启动 GEC 交易平台,用户(特别是大型工业企业)出于碳披露、绿色采购等目的购买 GEC。根据能源研究会数据,2024 年 GEC 成交价区间为每 MWh 80-130 元,折合约 0.08-0.13 元 /kWh,是传统电价的一大补充。
2. 碳市场交易。如果新能源项目用于替代煤电,并被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,则可以获得「碳资产」收益。截至 2024 年底,全国碳市场价格约为 70 元 / 吨 CO₂,每度绿电约减排 0.8-1.2 千克,理论收益在 0.05 元 /kWh 左右。
3. 峰谷电价调节与需求响应激励。发电企业与高耗能用户签订用电调节协议,在高峰期减少负荷或向电网反送电力,可获得额外补贴。该机制在山东、浙江、广东等地试点中推进较快。
在这种机制下,新能源项目的盈利能力不再取决于「我能发多少电」,而是:
- 我能不能卖到好价钱?
- 我有没有长期买家?
- 我能不能削峰填谷?
- 我有没有储能或其他调节能力?
- 我有没有可交易的绿色资产?
过去那种「抢指标、靠补贴」的项目模型已经走到尽头,未来新能源企业必须具备金融思维、市场操作能力,甚至要像做衍生品一样精细管理电力资产。
一句话总结便是:新能源的「卖电」环节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,而是一场以电为媒介、与政策、市场、碳权、金融协同博弈的系统工程。
为什么会有弃电?
对于发电项目而言,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电站建得成不成,而是「建成之后卖不出去」。而「弃电」就是这个环节中最沉默却最致命的敌人。
所谓「弃电」,并不是你不发电,而是你发出来的电没有用户、没有通道、没有调度余地,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白白浪费。对一家风电或光伏企业而言,弃电不仅意味着收益直接损失,还可能连带影响补贴申请、电量核算、绿证生成,甚至影响后续的银行评级和资产重估。
根据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的统计,2020 年新疆的风电弃电率一度高达 16.2%,甘肃、青海等地的光伏项目也出现了 20% 以上的弃电率。虽然在 2024 年底,这一数据已分别降至 2.9% 和 2.6%,但在某些区域和时段,弃电依旧是项目方躲不开的现实——特别是在中午高光照、低负荷的典型场景下,光伏电大量被调度系统「压单」,等于发了也白发。
很多人会以为弃电是因为「用电不够」,但本质上它是一种系统调度失衡的结果。
首先是物理瓶颈:在部分资源集中区,变电站容量早已饱和,电网接入成了最大限制,项目批得下来却上不了网。其次是调度机制僵化。中国目前仍以火电机组的稳定性作为调度核心,新能源出力的不确定性让调度单位习惯性「限制接入」,以避免系统波动。再加上跨省之间的消纳协调迟滞,导致很多电虽然理论上「有人要」,但在行政流程和省际通道上「送不出去」,最终只能弃之不用。而市场层面则是另一套滞后的规则系统:现货电力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,辅助服务机制、价格信号体系都远未完善,储能调节、需求响应机制在多数省份尚未形成规模。
政策层面其实并非没有回应。
从 2021 年起,国家能源局已将「新能源消纳能力评估」纳入项目审批前置,要求地方政府明确本地「可承载指标」,且在「十四五」多项政策中提出要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、建设本地负荷中心、完善现货市场交易机制、强制配置储能系统以削峰填谷。同时,多地政府出台「最低消纳比例」责任制,明确新能源并网项目年均利用小时数不得低于国家基准线,倒逼项目方提前考虑调节手段。这些措施虽方向正确,但执行进度仍存在明显滞后——在很多新能源装机狂飙的城市,电网改造滞后、储能配建迟缓、区域调度权属不清等问题依然普遍,制度推动和市场配合的节奏仍不匹配。
更重要的是,弃电背后不是简单的「经济低效」,而是一场资源空间和制度结构的冲突。西北的电力资源丰富,但其开发价值依赖于跨省、跨区的电网输送和调度体系,而中国目前的行政区划与市场边界是高度割裂的。这就导致大量「技术上可用」的电力在制度上无处安放,成为一种被动冗余。
中国的电,为什么不能用于加密货币挖矿?
在大量「技术上可用、制度上无处安放」的电力被闲置的同时,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用电场景——加密货币挖矿,在过去几年不断以地下化、游击式的形式出现,又在某些区域重新获得「结构性被需要」的现实位置。
这并非偶然,而是某种结构缝隙的自然产物。加密货币挖矿作为一种高耗电、低持续干扰度的即时算力行为,其运作逻辑与弃风弃光的发电项目天然兼容。矿场不需要稳定的调度保障,不要求电网并网,甚至可以主动配合调度削峰填谷。更重要的是,它能把没人要的电,在市场之外转化为链上资产,从而形成一种「冗余变现」的通路。
从纯技术角度看,这是对能源效率的一种提升;但从政策角度看,它始终处于一种尴尬位置。
中国内地政府在 2021 年叫停挖矿,核心考量并非电力本身,而是其背后的金融风险与产业导向问题。前者关乎加密资产路径的不透明,容易引发非法集资、跨境套利等监管难题;后者则涉及「高能耗低产出」的产业评价,不符合当前节能降碳的战略主旋律。
换句话说,挖矿是不是「合理负荷」,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消纳了电力冗余,而取决于它是否被纳入了政策语境的「可接受结构」。如果仍以不透明、不合规、不可控的方式存在,那它就只能被归为「灰色负荷」;但若能够限定区域、限定电源、限定电价、限定链上用途,在合规框架内被设计为一种特殊的能源出口机制,它也未必不能成为政策的一部分。
这种再设计,并不是没有先例。国际上,哈萨克斯坦、伊朗、格鲁吉亚等国早已将「算力型负荷」纳入电力平衡体系,甚至以「电力换稳定币」的方式,引导矿场为国家带来 USDT 或 USDC 等数字资产,作为替代外汇储备的来源。在这些国家的能源结构中,挖矿被重新定义为「战略级可调负荷」,既服务电网调节,也服务货币体系重构。
而中国,虽不可能效仿这种激进方式,但是否可以局部、限量、条件性地恢复矿场存在权?特别是在弃电压力持续、绿色电力短期无法完全市场化的阶段,把矿场作为能源消纳的过渡机制、把比特币视作链上资产储备进行封闭式调配,或许比一刀切清退更贴近现实,也更能服务国家长期的数字资产战略。
这不仅是对挖矿的重新评价,更是对「电的价值边界」的重新定义。
在传统体系中,电的价值取决于谁买、怎么买;而在链上世界,电的价值可能直接对应一段算力、一种资产、一条参与全球市场的路径。在国家逐步构建 AI 算力基础设施、推进东数西算工程、建设数字人民币体系的同时,是否也该在政策图纸上,为一种「链上能源变现机制」留出技术中性、合规可控的通道?
比特币挖矿或许是中国第一次在「没有中间人」的状态下,把能源转换为数字资产的实践场景——这个问题敏感、复杂、但又无法回避。
结语:电力的归属,是一场现实的选择题
中国的电力体系并不落后。风能铺满戈壁,阳光洒满沙丘,特高压穿越千里荒原,把一度电从边疆送进东部城市的高楼和数据中心。
在数字时代,电早已不只是照明与工业的燃料,它正在成为价值计算的基础设施,是数据主权的根系,是新金融秩序重新组织时最不可忽视的变量。理解「电」的流向,某种程度上,就是理解制度如何设定资格边界。一度电的落点,从来不是市场自然决定的,它背后藏着无数次决策。电并不平均,它总要流向被允许的人、被认定的场景、被接纳的叙事之中。
比特币挖矿争议的核心,从来不在于它耗不耗电,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是一种「合理的存在」——一个可以被纳入国家能源调度的使用场景。只要不被承认,它就只能在灰色中游走、在夹缝中运行;但一旦被认定,它就必须被制度性地安放——有边界,有条件,有解释权,有监管口径。
这不是关于一个行业的松绑或封锁,而是一套系统对「非常规负荷」的态度问题。
而我们,正站在这条分岔口上,注视着这场选择正在悄然发生。
参考资料
[1] 中国政府网,《2024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》,2025 年 1 月。
[2] IEA,《Renewables 2024 Global Report》,2025 年 1 月。
[3] 国家能源局,《2024 年度能源运行报告》附录。
[4]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,《「沙戈荒」风光基地建设进展》,2024 年 12 月。
[5] 国家发改委,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,2023 年。
[6] 路透社,《中国 UHV 输电系统评估报告》,2025 年 5 月。
[7] Infolink Group,《中国新能源取消固定电价补贴解析》,2025 年 3 月。
[8] 国家电力调度中心,《华北电力现货市场运行通报(2024)》。
[9] REDex Insight,《中国统一电力市场路线图》,2024 年 12 月。
[10]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,《2024 年度电力行业报告》附表。
[11]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,《西北弃风弃光情况通报》,2024 年 12 月。
[12] 能源研究会,《绿色电力证书交易试点观察报告》,2025 年 1 月。
[13] CoinDesk,《哈萨克斯坦挖矿政策调整分析》,2023 年 12 月。